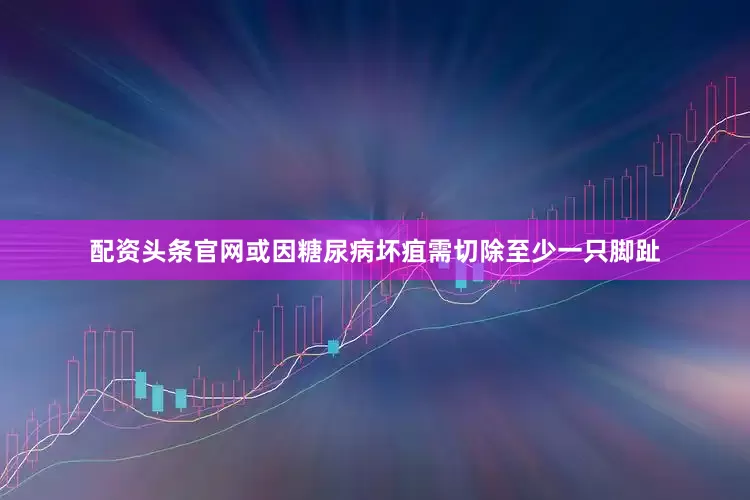【革命世家童年的牺牲分离记忆】
谁能想到,这位总说自己“像讨饭的”老太太,打小就没尝过几天“特权”的滋味。1924年她生在法国巴黎,父母是李富春和蔡畅——那会儿两人都是刚在欧洲投身革命的年轻人,根本顾不上孩子。没多久,她就被送回国内,跟着外婆葛健豪过活。外婆也是个了不起的女性,早年带着子女赴法留学,在那个年代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。
5岁那年总算跟父母在上海见了面,可团聚的日子比想象中冷清:父母整天在外忙革命,她常被反锁在屋里,饿了就啃油条烧饼,几天都说不上一句话。7岁时母亲蔡畅总算给她买了件新衣服,还是聂力过生日,顺带扯了块布做的连衣裙——那是她记忆里第一件不属于“旧衣服改的”衣裳。她后来总说,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5年,“实际上就像个孤儿”。
展开剩余82%【苏联岁月:从李特特到医疗员】
1938年,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子女,她被送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。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,卫国战争就打起来了,学校停课,她跟着大家上山伐木,进工厂造子弹,后来又被分到战地医院当护理员,编号A-247。那年她才16岁,在前线战壕里给苏军伤员换药、喂水,见过最残酷的场面——伤员的断胳膊断腿堆在一边,她得和其他人一起收拢了挖坑埋掉。
仗打完了,听父母的建议学了农业,在苏联期间和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结了婚,生了孩子。在那儿,没人管她是不是“副总理的女儿”,她就是医疗员A-247,一个在战火里熬过来的普通年轻人。
【放弃机关扎根艰苦土地】
1952年她从苏联回国,1955年春,刚生下儿子三个月,组织上想安排她在北京机关工作,她摆摆手拒绝了——那会儿北大荒正号召青年去开荒,她揣着孩子就上了火车。住的是茅草房,墙是泥糊的,屋顶漏雨,她和几个女同志自己搭大通铺。夏天蚊子成团,孩子嫩胳膊嫩腿被咬得全是红包,夜里哭个不停。她没奶水,那会儿物资缺,奶粉见不着,就把馒头烤得焦黄,磨成粉调糊糊喂孩子,孩子吃了拉绿屎,她心疼得掉眼泪也没吭声。
后来中苏关系紧张,她和俄罗斯丈夫感情也淡了,办了离婚手续,一个人带着儿子过,白天下地干活,晚上哄孩子,再后来遇到现在的丈夫,又生了个女儿,一家四口挤在茅草屋里,日子照样过。
没过几年,新疆需要搞核效应实验,她又主动申请调过去,说“越艰苦的地方越需要人”。去了才知道,戈壁滩上没水没电,白天穿防护服在沙地里埋电缆,太阳晒得防护服能拧出水,晚上打着手电筒记数据。有回一阵大风把零件吹跑了,她追着跑了三公里才捡回来,手臂被沙砾刮得全是血道子,用布条一缠接着干。组织上看她辛苦,想调她回机关,她还是那句话:“这儿离不开人”。
【退休“化缘人”20年筹钱】
1988年退休,有人找她去特区办公室挂个名,说“不用天天来,每月领工资就行”,还有家公司请她当名誉董事长,配车配秘书,她都摇头——“坐办公室喝茶不是我的事”。转头就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,成了终身理事,一分钱工资不要,整天背着个旧布包往外跑。
她翻出父亲李富春生前的老通讯录,又托人打听老战友、老部下的电话,记了几十本电话本,从中央领导到地方企业家,号码密密麻麻写了又改。打电话过去,开头总说“我是李特特”,对方客气几句,一听是要“化缘”给贫困地区修路打井,语气就变了——“特特啊,最近手头紧”“这事得研究研究”,有的干脆挂电话。
去机关找老熟人,人家让秘书出来说“领导开会”,她就在走廊长椅上坐冷板凳,一等两小时,中午啃个馒头接着等。有回筹到笔钱给山区建学校,结果县里把钱挪去盖办公楼,她气得坐火车赶过去,堵在县委门口三天,直到钱追回来才走。
后来学乖了,不管捐多少,都盯着签协议:“打井的钱,先给一半买材料,井出水了再给另一半;盖学校的,钢筋运到工地付30%,封顶了付50%,学生坐进教室再结清”。
1995年基金会统计,她这七年跑了两百多个贫困县,筹的钱超1600万,帮四十多个村架了桥、打了水井,建了十二所学校、七个小工厂,两万多人靠着这些项目脱了贫。有人问她图啥,她翻着电话本里被划掉的号码笑:“他们讨厌我没关系,老百姓能喝上干净水、孩子能上学,就行。”
【扶贫:责任重构与时代坚守】
她总随身带着本大相册,里面全是贫困地区的照片:破教室漏雨的屋顶、孩子光脚踩泥路的脚底板、老乡家没水吃的土井,翻给企业家看,说“你看这孩子,冬天没鞋穿”。
扶贫款怕被挪用,她就盯着项目进度:打井的先给买管子的钱,井出水了再给剩下的;盖学校的钢筋运到工地才付三成,学生坐进教室再结清,自己算预算,一笔笔记在旧本子上。
有人请她挂名领奖、上宣传栏,她都摆手,说“我不是来出名的”。唯一接受的“扶贫基金会终身理事”证,被她用胶布贴在厨房门口,水管子滴着水,地板裂着缝,她住老家属院的小房子,说“换大房子要花钱,不如省下来给老乡打口井”。
每天早上起来先翻电话本,琢磨今天该给谁打电话“化缘”,晚上整理贫困县的材料,一忙就到半夜。
【反向人生:责任重过背景】
她一辈子没靠过父母的名字。放弃苏联的安稳、北京的机关职位,一头扎进北大荒的茅草屋、新疆的戈壁滩,退休了又背着布包当“化缘人”,被人讨厌也不撒手。
革命年代的“特权”,在她这儿从来不是享受,是牺牲的权、吃苦的权。住老家属院,厨房水管漏着水,地板裂着缝,却把筹来的钱全花给贫困地区的水井和学校。
2021年走的时候,没开追悼会,不留骨灰,就留下一箱子扶贫材料、磨破的布包,还有张“节余交党费”的存单——她用一辈子的“反向人生”告诉你:责任这东西,比什么背景都实在。
发布于:河南省盛达优配-盛达优配官网-郑州股票配资-股票配资免费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最正规的股票杠杆配资平台至于备受大家关注的中国男篮
- 下一篇:没有了